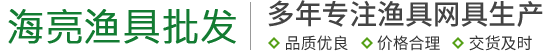商场门口张贴的法院执行公告像一块巨石,瞬间击碎了商户们的经营信心,也把这家上海老牌房企推向了生死边缘。
初夏的上海,位于静安区的XX商场一派繁荣景象,零售、教育、娱乐、餐饮等各种业态一应俱全。然而就在一年前,这座商场的产权方A公司背负近40亿元债务,商场面临被拍卖的窘境。
A公司创办于1995年,是上海最早涉足房地产开发的民营企业之一。近年来,受行业调整、关联担保等因素影响,公司财务状况恶化,银行贷款逾期,诉讼执行案件纷起,经营的商场被司法查封,陷入濒临破产的困境。
“很多购买了课程的家长,看到了执行公告后要退课,还有些直接到周边竞争对手的门店去了,压力太大了!”在商场二楼经营儿童体育教培机构的负责人刘某无奈地说。
恰在此时,A公司了解到上海新设立的庭外重组机制,决定尝试这一创新路径化解危机。
从财务上看,A公司已经破产了。但在感情上,公司管理层真不愿意让企业一破了之。公司除了这座商场,还有公寓、商铺、办公楼、车位等别的资产,也许还有盘活的可能。
A公司曾多次尝试和债权人协商和解方案,但由于债权人众多,“按下葫芦浮起瓢”,始终无法打破僵局。
2024年9月,A公司向新成立的困境企业服务再生平台寻求帮助,成为该平台受理的第一个庭外重组项目。该平台将多家专业机构纳入“企业重组官”名册,经推荐,A公司选定一家专业律师事务所担任企业重组官。
庭外重组的相对灵活性,是A公司决定提出申请的重要因素。企业希望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完成债务梳理、债权人谈判、投资人引入、重组方案表决等工作,为可能的破产重整打好“提前量”。
这样做能避免引起经营商户和周边消费人群的恐慌,有助于维持商场的正常经营,也能让企业有较为稳定的现金流生存下去,大幅缩减破产重组的流程时间。
企业重组官组建专业团队,全面梳理A公司资产、债务,制定庭外重组债权人议事规则,协助A公司与主要债权人开展多轮沟通。
重组伊始,不少债权人对于庭外重组以及企业重组官的概念十分陌生。通过与债权人、困境企业的一次次沟通,双方对庭外重组有了认识上的转变,逐渐建立信任。
历时5个月,专业团队完成近40亿元债务梳理,A公司在保持核心经营团队稳定和核心商业体正常运营的情况下,成功引入战略投资人,与超过三分之二的债权人签署《重组协议》,庭外重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市场化的定位避免了司法强干预,让庭外重组在‘阳光’下有序运行。”负责该项目的律师表示,“债务协商的效率越高、重组方案执行得越快,企业‘起死回生’的希望也就越大,无论对企业、员工还是市场都是多赢。”
庭外重组中心“投资人库”的平台资源聚集优势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企业重组官迅速对接浙江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A公司度身定制重组方案。
如今,A公司所持有的商场依然一派热闹的景象、商户正常经营、客流平稳有序。企业相关负责人说:“我们期待着‘轻装上阵’,重获新生。”
2025年1月,庭外重组中心终止A公司的庭外重组程序,依照其与破产法庭会签的工作备忘录规定,协助A公司向法院申请预重整,并出具“重组情况说明”,同时推荐原企业重组官担任预重整阶段的临时管理人。
庭外重组的工作成果往往需要与预重整、重整程序相衔接。一方面,庭外重组协议经过重整程序由法院审查并批准成为重整计划,才能获得更强的法律约束力;另一方面,庭外重组过程中各方达成的一致意见,能为预重整、重整奠定良好基础。
法院受理A公司预重整后,指导临时管理人加快推进庭外重组期间启动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债权审核等工作,并以《重组协议》为基础,制定重整计划草案。
根据《重组协议》的约定,司法重整的重整计划草案与庭外重组方案一致或未作实质性改动的,债权人、出资人在《重组协议》中表决同意的效力可延伸至预重整、重整程序。
这是将庭外重组中的谈判成果转化为司法程序的表决结果,能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提高了重整表决效率及成功率。
2025年2月底,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和出资人组预表决同意重整计划草案。该案转入正式重整程序,债权人会议同意原临时管理人继续担任管理人。
因有前期工作打下良好基础,重整程序中的债权申报、债会召开都十分顺利,债权人会议正式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法院于2025年5月裁定批准了重整计划。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俞强律师提示:庭外债务重组在我国立法层面尚属空白,其法律效力主要基于《民法典》合同编相关规定。债务人与债权人、投资人在庭外重组期间达成的重组协议本质上属于一种合同,是私法范围内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
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庭外重组协议中有关债权调整、中止执行、收益分配等内容的约定,只对合同的缔约方当事人发生效力,对于未参加重组谈判的人员则不具有约束力。因此,庭外债务重组达成的协议不能阻止异议债权人或者未参加重组协议的债权人的个别诉讼或执行行为。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俞强律师分析指出,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5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重整申请前,债务人和部分债权人已经达成的有关协议与重整程序中制作的重整计划草案内容一致的,有关债权人对该协议的同意视为对该重整计划草案表决的同意。”
这一规定为庭外重组协议效力在重整程序中的延伸提供了法律依据。但需满足三个核心条件:
一是协议内容一致性要求。重整计划草案必须与庭外重组协议内容保持一致,若对协议内容进行了修改并对有关债权人有不利影响,受到影响的债权人有权要求重新表决。
二是信息披露充分性。推定有关债权人表决同意重整计划草案的前提是债务人向有关债权人充分披露信息的情况下达成了有效的庭外重组协议,否则庭外重组协议可能构成欺诈或者显失公平而属于可撤销协议。
三是债权人异议权保障。当重整计划草案对协议内容进行了修改并对有关债权人有不利影响,或者与有关债权人重大利益相关的,受到影响的债权人有权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对重整计划草案重新进行表决。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俞强律师指出,当前我国庭外重组与司法程序衔接的创新实践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企业重组官”机制。参照法院破产重整阶段“指定管理人”的定位,设立“企业重组官”角色。困境企业在完成庭外重组后,庭外重组中心会向法院出具意见,推荐企业重组官继续担任临时管理人或管理人,以此保障司法程序与前期重组无缝衔接。
二是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制度。通过指导协调银行业债权人依规成立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按照“一企一策”方针,积极支持债务企业实施金融债务重组。
三是投资人资源平台建设。通过组建企业重整事务中心,遴选有重整价值的困境企业项目,聚合投资人资源,推动困境企业及早实现庭外重组。
一是财产保全困境。由于重组协议只对同意的债权人产生效力,而不能约束不同意的债权人,也无法阻止其他不参加协商谈判债权人的追债行为。在重组协议交易谈判中和重组交易完成前,不同意或不参加重组协议谈判的个别债权人随时都有可能针对债务人的财产进行诉讼或强制执行以偿债。
二是钳制问题。庭外债务重组不适用多数决表决机制,债务重组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可以征得参与重组的全体债权人一致同意。若部分参加庭外重组谈判的债权人未投“赞成票”,庭外重组协议或难以成立并执行。
三是制度供给不足。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庭外重组法律规章,相关规定主要来自最高院会议纪要等。这些制度政策缺少上位法依据,仅仅是政策框架,相关配套政策、实务指引等不够完善,离市场需求还有一定差距。
暑期临近,对从事儿童体育教培的刘某而言,又一个招生旺季来临,他正忙着接待来购买课程的家长:“峰回路转,商场的新投资人正在和我们协商签订新的租房合同,终于可以安心做生意了!”
随着上海加速打造国际法律服务港,搭建集发布特殊资产项目、促成困境企业与投资人对接为一体的平台,将有更多困境企业通过庭外重组与司法程序衔接机制获得新生。
上海破产律师俞强律师指出,庭外重组与司法程序衔接通道的打通,为更多困境企业赢得了生机,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再探新路。